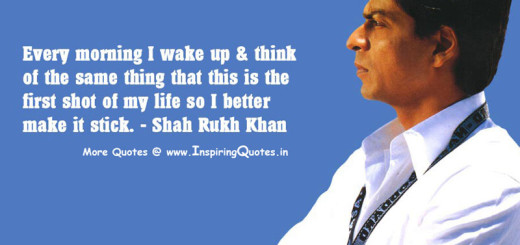冰点 | 我在美国踉踉跄跄的日子
在美国佐治亚理工大学给留学生办的英语课上,我一眼就注意到了鹿湘。
不知道为什么,国内出来的年轻人都有类似的气派。鹿湘是个小巧的女孩,有大大的笑脸,说起英语来清晰又响亮,碰到事情,很习惯地对人解释“我们中国人如何如何”。她会主动去对外国同学科普港澳台与中国大陆的关系,这样的事情,我在十八九岁刚跟外国人打交道的时候也做过;课程的内容有一项是写博客,她写道,她的梦想是做一个中国文化的“沟通者”,让外界了解真正的中国。
事实上,要沟通,就先得了解外界。我和鹿湘的身份,都是这所学校学生的配偶。理论上来说,我们唯一的任务,就是适应本地的生活。但就这一件,我们也完成得踉踉跄跄。
有一天,鹿湘向我提起了她在国内的生活:在一个二线省会城市,在父母不同意的情况下向同事借了几万块钱误打误撞买下了一套小公寓,现在房价已经翻番;就凭一份本科学历,一个女孩子能够挣到独立的生活,能过得特别硬气,一点不用看别人的脸色。
再说起现在的生活,她的眼神黯淡下来:“国内中等收入群体一年收入20万元的生活,比这儿的中产有意思多了。”
这是我在美国两年,常常听到年轻一代表达的一种观点。有时候我会忍不住问对方,是不是忽略了美国生活某种丰富的可能性。但同样地,我并不奇怪,所谓“美国梦”勾勒出来的物质生活画卷,单调,有局限,对现在出国的年轻人来讲没什么吸引力。
每当有人问我“华人在美国的生活究竟怎么样”,我都想跟他们讲讲姚医生和肖先生的故事。
这两位都是上世纪80年代末出国的那批年轻人,身揣着少得可怜的积蓄来到美国,如今,都过上了典型美国中产的生活——拥有郊外独立屋、汽车,从一无所有到拥有一份体面的中产阶级职业……
但让我感到新奇的并不是这些。
真正拉开差距的,是在房与车之外的生活。
第一次听说肖先生,是在一个留学生公众号上读到了他在“第二届北美清华校友大会”上的发言。这位清华大学1981级计算机系的毕业生,将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解释成两点:“要照顾好自己和家人;要回馈和改变自己的社区、国家和世界。”
“我觉得我们几乎每个校友都做到了第一点,也就是照顾好了自己和家人。我们在世界各地的清华人,从总体来讲,经济收入、子女教育不输给任何学校的毕业生。”肖宇在校友大会上问道,“但我们每个清华人是否做到了第二点?我们是否要等到成了比尔·盖茨之后,才想要关注社区和改变世界?”
“如果我们每个清华人做到这两点,我们清华校友作为一个整体就能在各个层面和社区发挥影响,我们整体对社会的贡献,就会远远超过上午坐在主席台的那几位。”
肖宇是个身材壮实、肤色黝黑的中年人,北京人,大嗓门,说起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就滔滔不绝。读到这篇发言几天后,我在亚特兰大一间韩国烤肉馆里见到他。他回忆起自己第一次体会到“服务社区”的概念,是刚到美国那时候。他在佛罗里达州上学,有天听说当地华人团体急需一个翻译,目的是为一批因为偷渡被抓捕的华人提供法律援助,他自告奋勇地去了。
等见到了那个“华人团体”,他大吃一惊:对方看起来完全不是东亚人面孔。
他问:“你们会说中文吗?”
对方不会。
“你们去过中国吗?”
没去过。
“那你们还要管偷渡客能不能得到法律援助?”
这些都是来自牙买加的华裔。虽然这辈子没踏足过中国的土地,也不会说中文,却还有那股子“同气连枝”的劲头,义务为偷渡而来的华人提供援助。
“美国的这个生活啊,就是,表面上看貌不惊人的——高楼大厦也没多少,电线杆还是木头的……实际上,讲究多着呢。”他说。
在美国生活的这20多年,肖宇迷上了研究美国人生活细节里这种别具一格的“讲究”。比如,社区里每家的花园形态各异,但都遵循着“没有裸土”的准则,家家户户都得买树皮或松针覆盖住花坛里的土,因此风刮过不会起尘土;路边的木头电线杆,看着都特别破,一条条电线晃晃悠悠挂着,看着好像一百年没动过的模样,但其实维护成本特别低,特别省纳税人的钱。政府要在社区里建商场,大家都跑去反对:不欢迎商业机构进驻,晚上会吵着我们。
孩子从公立小学读到公立高中,都是免学杂费的,家长要负担的就是每天2美元一份的午餐;这午餐的饮料,还不准碳酸饮料公司来赞助,得是橙汁或牛奶这种健康饮料。当然,要是家庭收入低于一定水平,午餐也是免费的。
每天早上,校车接人也是不同的:小学的校车会停到每个学生家门口,中学的校车则会停在路口,大孩子们需要多走一段路,但因为停车站点少,校车效率也更高。
在肖先生看来,国内一些人提起美国,总爱讨论什么“民主的细节”,这其实不是他的美国邻居们在生活里最看重的——他们最看重的是“自由”与“公平”。当然,自由也意味着责任,每个人都得把自个儿的事情处理好。如果忘了在花坛里撒树皮,会被社区罚款,如果毫无理由地不让孩子上学,也要面临国家“暴力”机关的问候。类似的细节会给生活添不少麻烦,但老肖觉得值:“给你免费校车,给你免费午餐,课本也给你免费了,你再不来上学,我把你逮了,也不算冤枉吧?”
即便到美国多年,肖宇还是能发现新的、意想不到的细节。前两年,外甥来美国,肖宇稀里糊涂地带着他去了一趟家附近的公立高中,原本只是想问问学校:“外甥这情况能在这儿上学吗?要办什么手续?”
询问的结果让他大吃一惊。学校的老师说,按照义务教育的规定,学区里的孩子来了就必须得上学。问题是这会儿都快期末了啊,让这孩子现在考试,貌似不大公平。
“要不这么着,你们就当今天没见过我,这孩子你带回去熟悉下英文,等下学期开学时候再来,怎么样?”一番思索后,老师决定卖老肖一个人情。
去年圣诞,我在休斯敦见到了父亲的挚友姚医生。在机场上,我一眼就认出了这位斯文的中年人,虽然出国已近30年,身上还有挥之不去的江浙人气质。
姚医生和我父亲,都是恢复高考后第二年,也就是1978年,考上苏州医学院(现苏州大学医学部)的应届高中生。报到第一天,在一群大龄同学之中,我父亲敏锐地找到了这个和他一样才16岁的小伙伴,便与对方商量着说,要不一块儿去观前街转转。
“从学校里走到观前街要多久?”姚医生问。
“为什么要步行?坐公交车啊。”我父亲很惊讶。他后来才知道,姚医生的老家是长江中心的一个小岛,岛上没有任何公共交通工具。就这样,姚医生第一次坐公共汽车,是和我父亲一起去观前街。
姚医生的前半生,更像是一个励志典型。来自乡村的少年,考上大学,又考上了北京的研究生,然后获得一个出国进修的机会。1988年,姚医生第一次见到美国留学生住的宿舍,被满屋子的家电惊呆了:有电话、空调、小冰箱,还有电视机——这不是高干宿舍才会有的东西吗?
放假的时候,他和几个同学一块儿开着一辆漏风的N手车去佛罗里达州旅行。几个30岁左右的大老爷们儿,在迪士尼乐园里流连忘返:天底下居然还有那么好玩的地方!
像小蛋糕似的美式松饼,把蜂蜜或果酱浇在上头,味道可香,姚医生一下就喜欢上了。
他领着2000多美元的微薄工资,但德克萨斯州物价便宜,一个月房租只要400美元。剩下的钱换算成国内的货币,在当时看来,就是一笔巨款。到美国一年多之后,在北京当护士的妻子告诉他,医院要外派她们出国,去约旦工作。沉吟片刻后,姚医生问:“如果非得要出国,为什么不来美国呢?”
夫妇俩现在都很感激,医院没在办护照的事情上为难她。
其实说到这儿,命运最难测的部分就展露出来了:他们离开,也就错过了国内接下来30年的飞速发展期。现在,在美国做研究的学生月薪还是在2000美元左右,但在国内,几乎找不到什么东西,还能维持30年前的价钱。上世纪80年代末,肖宇在中关村见到过联想公司开出1000多元人民币的高薪招人,而他毫不犹豫地出国了;当姚医生咬牙下苦功夫用英文考取美国行医执照的时候,与他同一届的大学生,在国内普遍受到重用,如今正是国内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
我不止一次见过国内的中年大V发网帖讨论这一现象。大体上,人们比较后得出结论:现在国内的生活水准都赶上去了,有些地方比国外更便利。
从表面上看,在国内的同学们,与姚医生在美国的生活条件,差别已经不大:他在郊外的房子连地价,也就40多万美元,和国内二线城市的别墅差不多;老家家里开一辆中高档品牌的车,也和他的差不多。看起来,姚医生的日子过得还更朴素点,他的别墅内部只是简单的瓷砖或地毯铺地,油漆刷墙,没有大理石地砖,没有水晶灯,没有富丽的墙纸,没有任何看起来彰显财富的标志。
但当姚医生一家去教堂庆祝圣诞时,某种显著的差异出现了——华人社区一年给教会的捐款,是一个令我咋舌的数字。
当地人的解释非常平淡:“慈善捐款可以抵税,大家就倾向于捐钱了。”
除了捐款,姚医生也在业余时间参加当地的义诊活动。曾经乡村里走出来的少年,如今每次回中国,几乎都是为了去某个不知名的山沟、农村做义诊。
这说起来,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就是业余时间里做他想做的事情。
他说,年轻时,也曾日日焦虑,总觉得生活里所有的成就都得靠自己去奋斗努力,但在某一刻,突然就放下了这些执念,相信命运自有好的安排。
我想这真是很有意思,这些从两手空空到步入中产阶段的中年人,他们过的是这样一种生活:也在尽情享受,并不排斥物质。只不过,要是把他们生活中要关心的东西排一排,房子,或者钱,都还排不到最前面。
刚到美国的时候,我还带着股焦虑,总会跟人聊房子。渐渐地,我发现这个话题没有听众。不管是美国人,还是在美国多年的华人,都不理解我的焦虑——既不能理解没有房子时,从一个出租屋流落到另一个出租屋的辛苦;也不明白冒出买房的主意后,一颗心跟着房价起起伏伏的煎熬。
这不是因为他们修为深厚看破红尘。只不过是,多年习惯了宽裕的生活,这些人的注意力,早就不在物质上了。
但是,这就够了吗?
如今的生活,可并不是顺理成章就能拥有的。
就在1982年6月23日,姚医生赴美仅仅6年之前,在底特律一家汽车工程公司工作的华裔青年陈果仁,被一对Ronald Ebens白人父子打死在街头。事发前,他们曾在附近一所酒吧起过冲突,双方打斗的时候,有人听到其中的白人中年男子吼了一声,“就是因为你们这帮小兔崽子,我才丢了工作!”
那是上世纪80年代,正是日本汽车大举冲击美国市场,导致美国汽车公司不得不裁员的年头。
陈果仁被打死,只因为对方搞不清“日本人”和“中国人”有什么区别。
“亚裔是美国人中最孤独的群体。上世纪80年代的集体政治意识已经被一种无声的、无人理会的孤立取代。那种孤立来自这样一种认识:你可以出生在美国,你可以成绩优异、经济条件优渥,但你仍然感到在这个国家的公共话语中无足轻重。”
2017年年底,我在《纽约时报》网站上一篇长篇特稿中读到了这段话。那篇报道讲述了华裔大一新生邓俊贤在亚裔社团的入社仪式中被围殴致死的故事。虽然是一则发生没多久的新闻,但撰写这篇报道的韩裔作者花了很大的篇幅回顾“亚裔”的认同在美国如何被塑造。
“‘亚裔美国人’是一个大体上没什么意义的词汇。没有谁是说着‘亚裔美语’长大的,没有谁和自己的亚裔美国家长一起吃亚裔美国食物……但我们基本承受着一些共同的刻板印象——虎妈,音乐课,不经审视的通往成功之路——不管它们被如何定义。比起中国或日本移民的子女,我自己作为韩裔的成长经历,其实与美国的犹太人及西非移民的子女更像。但我和前者心怀同样的焦虑:我们中如果有一个被按在墙上,接着极有可能轮到另一个人。
歧视,是把亚裔美国人联系起来的东西。
1982年,陈果仁被殴打致死后,当行凶者仅被处以缓刑及3000美元罚金的时候,抗议者纷纷涌上美国城市的街头……把人们团结起来的是这样一种意识:如果进口自日本的汽车可以让身为中国移民之子的陈果仁被杀,那么‘亚裔美国人’身份的概念就有其影响。”
陈果仁1955年出生于广东,长到五六岁的时候,被养母余琼芳带去美国。1982年,当他和几个朋友走进底特律一家酒吧庆祝最后的“单身之夜”时,他已经长成了一个典型的亚裔美国人的模样:有着毫无负担的爽朗笑容,留着那个年代流行的吹高刘海、类似“飞机头”的发型,还能说一口地道的美式英语。当时他正在一所大学里学习机械工程的课程,同时打两份工,以求尽快攒够钱买房子——下个星期,他就要结婚了。接下来,酒吧发生了殴打事件。他的婚礼被改成了葬礼。
到这时候为止,华人社区都还很平静。打人的这一对父子被直接逮了起来,看起来是个没什么疑问的案子。但随后在法庭上,他俩以“认罪”的代价,被判缓刑3年和罚款3000美元。
主审法官觉得,这就是一个酒吧斗殴案件,眼前的两名嫌疑犯虽然喝高了以后干了点蠢事,但他俩看起来都是好人,“不是那种应该关到牢里去的人”。
“陈果仁的案子把亚裔美国人逼进了为民权奋斗的意识形态。”后来有人这样回忆说。
现在人们说起美国的华人,总会想起“模范少数族裔”或是“勤勤恳恳”“努力工作”这样的印象。但如果真正回看历史,华人在1848年左右便已经大批进入加利福尼亚务工,而“模范少数族裔”的称号则兴起于20世纪中后期。在那之前的100多年里,并没有人觉得亚裔“模范”,或是比其他族裔更有能力取得显著的社会经济成就。在《1965年移民与国籍法》之前,亚裔移民都没有像现在这样容易迁居美国的机会。
不少学者相信,华人在社会地位和工作机会上的突出,与美国在上世纪60年代之后,政府不得不通过一系列民权法案,给予少数族裔更多权益有关。
可以说,那个时候,美国主流社会也才刚开始学习,如何接纳亚裔移民。
我也是在读到《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时,才意识到,就算政策性的歧视都已经被废除,少数族裔还会面对这样的问题:“你再优秀,仍然感到在这个国家的公共话语中无足重轻。”
“他的死亡是一个重大的觉醒时刻。”韩裔电影导演崔明慧告诉《纽约时报》的记者。“这件事刺激了很多人,他们表示无法再忍受下去,不能就这么放任自流,必须有某些立法或政治要求。”
亚裔社区大规模的游行、抗议换来了陈果仁案在民权法庭上的另一次审理。1987年5月1日,陪审团最终认定这对白人父子对陈果仁的袭击行为并不带有种族仇恨的动机,但是要求他赔偿150万美元给受害者家属。
4个月后,陈果仁的母亲余琼芳离开美国,迁居广州。
2012年,陈果仁案发生30周年之际,一些美国记者回访了在美国乡间低调生活的Ronald Ebens。他说,30年前的事情,是一件不该发生的意外,他很抱歉。
因为一直没有正式工作,他从来也没有付过民权法庭判决的那150万美元赔款。
如今已经不是陈果仁案的时代了。美国华裔中涌现出了像朱棣文、吴恩达那样知名的科学家,关颖珊那样的体育英雄,以及赵小兰、骆家辉那样的政治人物。城市里的新一代已经能够把东亚各国分得清楚,并且在问出“你从哪儿来”这样的问题时有默契地只讨论出生地而不纠结祖上更远的文化背景。
但是我依然不确定,在这个国家的公共话语体系中,他们的分量有多重。而这重量,又会对他们的生活有多少影响。
唐纳德·特朗普刚刚当选总统的时候,我在亚特兰大一次活动中,与现场的华人聊天,提到许多家庭最近遇到了两代人为了特朗普而意见不一致的现象,现场一位有着体面职业的知识女性微微皱着眉头解释了一句:“这些年轻人,他们和我们不一样——他们已经是美国人了。”
在《纽约时报》那篇关于亚裔社团围殴新社员致死的长篇报道中,一个王姓学生告诉记者,在加入大学里的亚裔兄弟会之前,他对亚裔在美国的历史没有任何了解;他从没听说过陈果仁案,也从不知道“二战”期间,最高法院曾经支持罗斯福总统的政令,把日裔美国人关进集中营。这些案子在纽约中学的课程中,是一片空白,当理解了这些——一部分是被社团所扭曲过的历史事件——之后,他感到了莫大的沮丧和不平。
“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会忽视某个种族。有时候,那感觉起来就好像是在说,亚裔没有那么重要。”他说。
在另一篇《纽约时报》书评中,亚裔作者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长滩分校社会学教授奥利弗·王也表达了类似的思考:“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亚洲移民威胁到白人劳工时,我们是被鄙视的少数族裔;可是自冷战以来,我们又被称为‘模范少数族裔’,用来稳定学术界精英的信心。这种标签变换之随意,显示出我们的社会地位并不可靠,它附着于我们在别人心目中的功能:先是廉价劳动力,现在是把其他有色人种社区都比得自愧不如的超级优秀学生。”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对肖宇在社区内的努力大感兴趣。
他是那种会花15美元上网报名参加“市长年度报告早餐会”的热心市民;是市议会辩论时少数会在现场的华人观众;是那种会支持妻子去当陪审员的丈夫(一般华人家庭对这一需要旷工好几天的“光荣义务”都敬而远之)。
他也会利用朋友圈这巴掌大的地方,呼吁大家去发出自己的政治声音:“对住在亚特兰大北面几个城市的华人,4月18日国会第六选区的补选比总统大选更为重要。总统选举全州计票,人口比例1%的华人没有任何作用。但是第六选区的亚裔人口占10%,选出的国会议员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直接影响华盛顿一系列政策投票……除了自己投票,要马上鼓励和帮助上大学的孩子办理邮寄投票。孩子是我们的未来,通过孩子们的参与,让我们华人的政治声音最大化。”
“这也是美国人追求的一部分: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总统,无论种族、年龄和经验。”
他所在的约翰溪市,原本是亚特兰大的一部分。10多年前,因为市政府收税多,公共服务却总跟不上,大伙一合计,干脆直接关起门来自己干。
就这么样,约翰溪成了一个有四分之一华人居民的新城市。时间一长,肖宇就觉得很微妙:社区里的华人那么多,但大家都对公共事务不感兴趣,于是从没见过跑华人区拉票的政客。与此类似,学区里高中成绩最好的前20名全是华裔小孩,但家长协会里不见一个华人家长。
他就在这个时候开始思考“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之间的关系。在大亚特兰大都市圈,约翰溪几乎是最安全、房价最高、家庭平均收入最高的社区,华人聚居于此,说明大家都在这个国家取得了成功;那么,为什么不尝试去为社区出一分力,为什么不抓住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呢?
肖宇知道用自己行动去改变他人的滋味。他送儿子参加童子军活动,活动有一项,是家长和孩子一起去野营。在野外,他们做的饭,让社区的其他人一改“中国菜奇奇怪怪、味道难闻”的偏见。哪怕后来孩子已经成年,不再参加活动,肖宇也还会给亚特兰大的童子军总部教授“做好世界公民”的课程,比较不同国家之间的政治制度。
就这样,他们社区的童子军团队里有了更多亚裔团员。
女儿上中学时,肖宇支持她创办了一个“手拉手中文文化学校”,专门为当地被白人夫妇收养的华裔小女孩教中文,帮助她们接触中国文化,让她们对自己所属的文化有了更多自信。
另一回,他看见社区里的道路边新增了很多垃圾桶,便去打听:谁给放上垃圾桶?会花大家的税款吗?
社区领导让他放心:商业公司赞助的,不花咱的钱。
可他接下来一个问题,让领导傻了眼,很快撤回了这批垃圾桶:“垃圾桶是送的,那他们附送清理垃圾桶的方案了吗?这笔钱怎么算呢?会摊派到居民头上吗?”
生活不就是在这样的改变后一点点变好的吗?
不过,现实更有可能是这样的:肖宇的妻子陈苑生,曾在社区内的中文学校办了个“男儿要当童子军”的讲座,现场门可罗雀,听者寥寥;几年后,儿子考上了哈佛大学,还是一样的内容、一样的主讲人,能容纳200人的屋子,一下被挤得爆满。
纽约街头
即便知道了这些在美多年的华人的故事,把目光投回生活里,鹿湘和我面对的亚特兰大的社区,与肖宇和他家人面对的社区,也还是不同的。
我一度对自己总是孤零零的状态感到沮丧,后来在休斯敦,我听说了姚医生太太在上世纪90年代初来美国之后的经历:因为人生地不熟,在美国的第一年,她都没有去饭店里吃过饭;为了利用有限的资源学英文,她把《音乐之声》这部电影看了100多遍。
“最能提升英语水平的机会就是准备考试。”她告诉我,“每次考试之后都感觉自己进步了一大截。就这么一次次考过来。”她考上了美国的护士执照,在德克萨斯州医疗中心找到了工作,就算开始上班了,也常常搞不清楚电话那头医生用极快语速说出来的药名究竟是什么。医院不会容忍错误。她感到孤独又疲惫,每天下班出门的时候,都要对自己说一句,“我讨厌这个地方”。
“突然有一天,我不再说这样的话了。然后发现,自己已经适应了这个环境。”姚太太说。
我们这两代人,生活已经有了许多不同。
肖宇和陈苑生刚来美国的时候,能对街上的路灯看半天:怎么路灯都这么亮?而且夜里不关灯?那么空的大街、大楼,夜里都不关灯,闪闪地亮整晚。而我和我先生第一次抵达纽约的时代广场时,满心都是疑惑:不就是一圈广告牌吗?为什么大家都要来看这样的地方。
姚太太能在寂寞中把《音乐之声》看100遍;而我们能够连上互联网,无缝对接国内的大小媒体,接着观看自己熟悉的电视台,就像与国内地理上的距离并不存在一样。
但即便物质条件差异如此之大,某些感受依然是共通的。比如姚太太在美国的这个时刻:等到某天不再咬牙切齿地说出那句话,她才意识到自己已经适应了。
他们努力过,付出过,最后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姚医生生长在长江中心的一个小岛上面,岛上就只有一片竹林、两条村巷。小时候,他最羡慕村里的赤脚医生,1978年,当他有机会考大学时,便在志愿表上填了一堆医学院。那之后,他的每一次人生转折——不管是考研、考美国的执业医生资格,还是办自己的诊所,都是顺着这个最初的梦想而去的。
原文刊载于《中国青年报》2018年08月22日 12 版
作者 / 黄昉苨